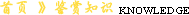
古玉飞天佩的饰用方式初探
飞天是佛教造型艺术的一个题材独特的品种,它是为诸天服务的小神。在佛教造型艺术体系中,是作为陪衬、装饰而存在的。然而,人们对它的欣赏、喜爱,应该不仅仅局限于此。笔者在此分析玉飞天各个时期的特征,给藏家在投资上以借鉴。
唐飞天佩
隋代统一前的近4个世纪,是佛教在我国发展的时期,也是中国玉器工艺史,处于两汉玉器大发展和唐宋玉器大繁荣之间的低谷时期。这个时期的佛教和道教在南北朝时期与儒教分庭抗礼,儒家那种赋予道德内涵和礼制观念的玉器体系已彻底瓦解。这个时期的玉器无论从品种上,还是数量上都比前期大为减少。它的前面是以礼仪玉、丧葬玉为主,充满对礼、神崇拜的玉器制作时代。它的后面是以装饰玉、实用鉴赏玉为主,以张扬人性爱好,以把玩件、摆设雅件等的玉器时代。
唐代近300年的统治,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。给唐代玉器迎来了又一次蓬勃发展的机会。吸取了大量的外来营养,玉雕着重向写实方向和装饰化方向发展。魏晋以来广泛流行的佛教,在隋唐时期达到高峰。佛教玉器的应时而起,是佛教进一步中原普及化、世俗化的重要例证。自唐代开始,佛教玉器主要有玉佛和玉飞天两种。唐玉佛多见于文献记载,而目前考古出土的真正意义上的玉佛实不多见。
飞天不仅仅作为装饰娱乐而存在。若使它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,其中应该具有更深的佛教信仰意义。佛经上说,每当佛讲经说法时,飞天们都会脱掉上衣,凌空飞舞,奏乐散花。飞天见到佛主时的那般皆大欢喜的样子,使古代玉雕作品飞天的佩带人,也具有了同样的崇拜佛主、供奉佛主的敬仰属性。玉飞天唐代出土的不多,多见的是宋辽金以后。考古出土也没有多少。故宫清藏传世品中能见到的,在形制尺寸和器物的厚薄纹样上,与考古出土玉飞天有着不少区别。主要区别在传世品的形制偏大点,片状厚度比出土器明显偏厚。然而,在器体扁平略成三角形的外观上,出土器与传世品玉飞天都有着十分接近的共同特征。
在文博界与收藏界,对玉飞天的使用场合、佩带方式一直是个未揭开的谜。一般认为玉飞天的用途和佩带方式,不是佛龛楣、坛座等处镶嵌用玉,就是佛教徒佩带的避邪用玉。然而笔者认为它与佛教仪式中的“行佛”有关。
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,“行佛”这样的盛典就逐步形成了。“行佛”是佛教活动重要仪式之一,起源于古印度,一般在佛诞日及佛出家日举行。我国的佛教“行佛”仪式,早在《魏・杨炫之・洛阳伽蓝记》中就有记录。宣武皇帝景明年,建景明寺,太后造七级浮屠一所占地百亩,上自达官贵人,下至平民百姓都纷纷将自己的住宅舍出来作为寺院。4月7日,京师洛阳诸像皆汇聚此寺,至8日,先入宣阳门,后向阊阖宫,再接受皇帝散花献佛的礼仪。当时城内金花映日,宝盖浮云幡幢若林。其间有一金像辇,去地有三尺高,宝盖上四面垂金铃七宝珠,绘飞天伎乐于云表,共用百人举此像。名僧德众负锡为群,信徒法侣持花成薮,香烟似雾梵乐动天。这样的场景现如今在西藏喇嘛教寺院中,依然可以从保留着的一幅清代《弥勒佛行像图》中看见。其气势之磅礴、场面之宏大,与我国早期行像文字所描绘的一致,为世罕见。
“飞天”一词,在汉译佛典中,最早似见于西晋永嘉二年的《普曜经》。而汉译佛典中至今仍然找不到“飞天伎乐”的出处。在《洛阳伽蓝记》中所提到的“飞天伎乐”,应该是目前最早的将飞天的职责明确化,与伎乐一词并提的记录出处。是中土人根据佛教供养音乐的性质,而新造的名词。“飞天”是对应佛典中八部护法之一称“乾闼婆”“紧那罗”的歌舞散花之神。在《大智度论》中说:“乾闼婆是诸天伎人,随逐诸天,为诸天作乐。”而佛教东传后,信徒数量有增无减,逐渐取得了主要派别的地位,壁画图像中的飞天脱去了胡服,换上汉族女子模样,并随着佛教势力的扩大,世人则常把它归入了帝释天的专属门下,结合了中国古代道教文化中“飞仙”“嫦娥”“天人”“羽人”之说,以“吴带当风”之美,为它译成了非常好听的名字――“飞天”。
所以飞天应该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以来独特的儒释道兼修、多元化宗教信仰混合的形象,并具有形体夸张特征的产物。夸张与想象,只能以现实生活中的所闻所见,移花接木的结合和创造为依据的,决不是凭空而来。飞天以奇形异态却又富有人性的形象,在敦煌壁画中出现了许多。这些飞天形象大量吸取了民间舞蹈艺人的形体语言,寄托着人们对佛国的无上向往。《洛阳伽蓝记》中所提到的“皇帝散花”,与壁画中描绘的佛教盛典飞天散花的内容是一致的。在辽宁省朝阳市辽代北塔天宫里出土的玉飞天也说明,供
